撰文|走近動物園 責任編輯|蘇于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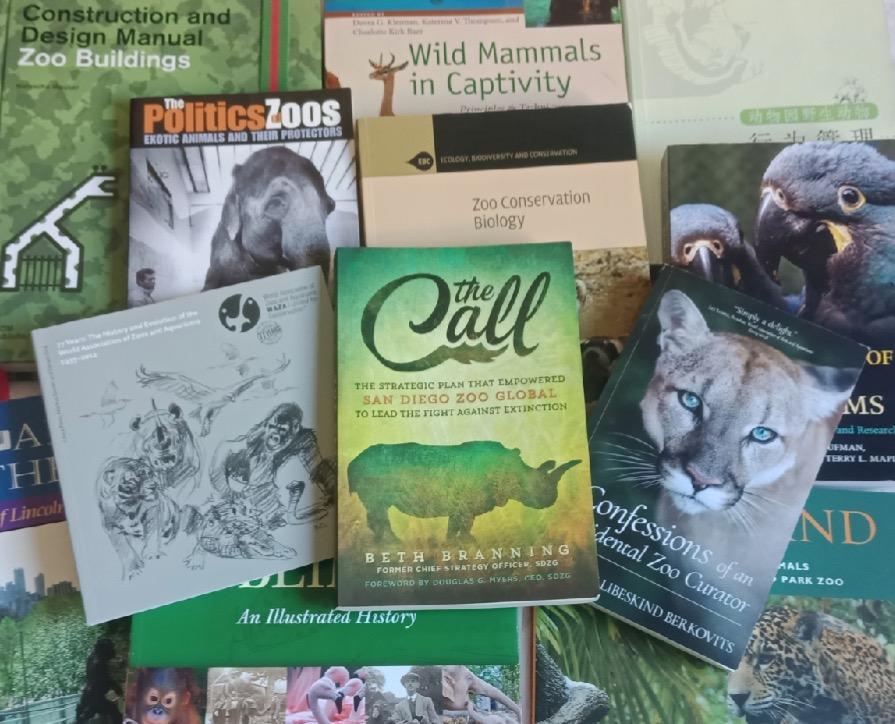 (The Call: The Strategic Plan That Empowered San Diego Zoo Global to Lead the Fight Against Extinction)
(The Call: The Strategic Plan That Empowered San Diego Zoo Global to Lead the Fight Against Extinction)
共享願景
知道要「做甚麼」之後,下一步就是將目標解構並逐項討論「怎麼做」以及之後的實行層面,這部分上至組織的CEO,下到只在週末排班的志工,必須凝聚所有相關人員的意念,產生一同促成轉變的士氣,但同時卻又牽涉到組織內部結構劃分還有事務規定等等,就連SDZG也是在The Lynx期間吸取了許多教訓與經驗,才找到組織內有效溝通的突破點,比集思廣益出vision時更甚,很考驗整個組織的是否能有效的做為一個整體來行動。
保育員、獸醫這樣能近距離接觸動物,在第一線「感受保育發生」的職位,在接納動物園樹立的新方向並付諸實踐等方面比較沒有隔閡,也能很快理解工作轉變對於實現願景的幫助。但包括設計師、財務專員甚至賣店櫃員在內的「後勤」分支,或許就會因為自認負責的項目無助於願景的實現,而難以被激發出與前線人員相同的動力。可若因此在轉變的過程中落下任何一個區塊,執行效果都將因為斷層感而大打折扣,這時,簡潔有力的願景就像燈塔一般,可以在討論僵持不下、迷失方向或者執行不如預期、引發矛盾時提醒參與者應該邁進的方向。
The Call執行後,如同mission中強調的「把專業結合啟迪」,對於「整體感」的塑造成了一大重點,將信念實踐在整個園區並加以散播,民眾才更能體會到園方的決心。
但要達成這些需求,另聘專員是無法滿足的,致力於賦予現有雇員更多「借力使力」的契機才是重點。以賣店櫃員為例,鼓勵他們把握遊客排隊的數秒空檔來「加深連結」,就算可能只是問問抱著北極熊布偶的小孩今天有沒有看見熊這樣再簡單不過的對話,或者主動在結帳時告知遊客動物園使用再生材質做為商品包裝的用心這樣的「舉手之勞」,從遊客那裡收到的反饋卻讓多數員工感覺自己似乎終於與動物園的遠大目標站到了一塊,有了與第一線人員同在一座保育教育機構裡奮鬥的實感。
就好比迪士尼樂園,裡頭的每一個雇員,就算只是打理園區街道的清潔員或者指路NPC,都經歷了紮實的培訓賦予他們面對遊客、出演「夢之國」的住民的「魔力」,不僅創造出良好的遊園體驗,也讓他們的「工作」變得更加鮮活,跟米奇米妮一起成為散播快樂的組成成份。
 ZSL London Zoo(左)跟Dudley Zoo(右)同樣致力於在動物展示之外的方面也向遊客傳達永續的重要性。
ZSL London Zoo(左)跟Dudley Zoo(右)同樣致力於在動物展示之外的方面也向遊客傳達永續的重要性。
另外,在對抗滅絕的戰役中,除了團結內部員工,拉攏民眾一同起身反抗更是重中之重,每年超過世界人口十分之一的潛在戰力(動物園遊客)無疑是一股必須善用的能量。在談到動物園的設計時,「沉浸感」是一個經常出現的字眼、被追求的目標,但在大多數的機構中卻往往只達成了一半,仿造動物原生地的展場、延伸到遊客面的植物與佈景、彷彿身處一場冒險的故事線,甚至導入讓遊客與野外族群產生連結的資訊,看似已經對「豐滿體驗」盡到足夠的責任,但卻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替在當下萌生的情感指引出路。
 雖然同樣飼養著食火雞,甚至鳳凰谷鳥園(右)還展示著更為稀少的單垂鶴鴕,遊客能接收到的資訊卻遠遠不及Chester Zoo(左)。
雖然同樣飼養著食火雞,甚至鳳凰谷鳥園(右)還展示著更為稀少的單垂鶴鴕,遊客能接收到的資訊卻遠遠不及Chester Zoo(左)。
許多動物園專注於為遊客提供「Take home messenge」,期望動物園能發揮指路的作用,但卻忽略了保育之於社會大眾的門檻以及看、聽、讀與做之間的巨大鴻溝,許多在動物園中激盪出的情感因而在take-home的過程中煙消雲散,保育力量的集結也於此中斷。
但實際上,想要「Empower」這些情感,作法其實再單純不過,包括開發《Biodoversity is US》這樣協助民眾將逛動物園的體驗融入進日常生活的應用程式在內,只要能讓遊客「在受到觸動的當下做出行動」,情報、情緒隨即與付出連結。無論是透過簡易的捐款箱,幫助遊客把財產投注到保育工作;還是發起campaign,讓遊客為動物園的下一步做出決定;或者在講述相關議題的解說牌旁增設任何形式的互動,比如海洋垃圾與塑膠回收站、貴金屬開採與舊手機捐贈、熱帶雨林與永續棕櫚油產品、溫室氣體與搭乘大眾運輸、水資源再利用與打水器……。
僅僅是提供遊客多跨出一小步的機會,與他人一同「讓保育發生」的實感,就能引導他們看向與以往不同的景色。
動物園,遠遠不只把動物給養好這麼「簡單」。
 對於水資源的再利用,台北動物園(左)與Chester Zoo(右)同樣在園內做出了表示,可惜前者缺少足夠的引導而後者缺少導向的目標,很可能導致遊客對議題的忽略。
對於水資源的再利用,台北動物園(左)與Chester Zoo(右)同樣在園內做出了表示,可惜前者缺少足夠的引導而後者缺少導向的目標,很可能導致遊客對議題的忽略。
動物園的商業與伴隨其生的社會責任
看到這裡或許已經有不少人注意到,這本《The Call》其實不過是將現代的商業思維套用進動物園之中,並沒有闡述甚麼過於超前的概念,但這樣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詳實記述「挑戰過程」的筆法也正是它如此「深刻」的原因。
它所呈現出的,並非是為了維繫大量支出並供應僱員與園內動物的溫飽——世界第一的動物園選擇為了五斗米折腰,妥協於那些能夠吸引人(錢)潮的歪路,最終落入商人窠臼的「劇情」,而是當一座動物園選擇回歸根本、審視自身經營方式後,會帶來甚麼樣的影響。
2001年,下定決心改變的Zoological Society of San Diego每年的營收是一億三千六百萬美金,這一數字,在2017年的SDZG增長為三億四千六百萬,在精進動物園本分的同時,將原先已被視為行業翹楚的「吸金功力」再創高峰,SDZG用行動證明,或許,一直以來人們看待「動物園商業」的方式從根本上就錯誤了。
專注於保育這般「公益事業」的動物園,長久以來一直蒙受「不能追利」的壓力,認為一旦將目標放向了營利,慈善就不成立,更甚者,被不分青紅皂白地批評到動物園的復育是以營利為目的。可事實上,就如同Dan Pallotta在他著名的TED演講中談到的:
非營利組織應該被允許去追求更大的「回報」,追求商業方面的成長非但不是對慈善的背棄,反而是負責到底的表現。
而美國著名的管理學家Jim Collins雖然在他的著作《Good to Great》中展示了他對於商業組織的理想模型,但不久後他便意識到這個模型的缺陷,並在《Good to Great and the Social Sectors》中補充了「市場的另一層面」,一個更多的投入同樣意味著更高的收益,但擁有會選擇將這些收益再次挹注回自身的願景而非口袋的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的市場。
雖然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無高低之分,但想達到「做保育的動物園」們追求的目標,後者顯然更加貼近他們的主張,所謂「社會企業」是指以解決特定社會問題為核心目標的創新企業組織,透過一般商業營運而非捐贈的模式在市場機制中自給自足,具備商業行為及社會公益的雙重屬性。在SDZG的案例中,他們期望解決的問題與核心目標是「終止滅絕」,而動物園則是商業營運模式的主體,透過提供「動物園」這一個服務,在自給自足的同時穩步朝著目標前進。
同時,正因為以動物園這樣一個在社會中提供「服務」且民眾得以「切身體驗」的形式存在,掌握了自身的影響力與聲量,才使得許多單憑保育團體的身分無法達成的對話,比如與大型跨國企業的「合作」成為了現實,從麥當勞到可口可樂甚至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世界上的動物園確實成功地吸引了商人的目光,「There will be no zoo without you」,絕不只是單純用來諂媚支持者的迷湯,而是鐵錚錚的現實:
「遊客」——永遠是動物園重要的組成成份
 Chester Zoo的美洲豹展館建造係由捷豹贊助,同時雙方也合作保育野生美洲豹的棲地。
Chester Zoo的美洲豹展館建造係由捷豹贊助,同時雙方也合作保育野生美洲豹的棲地。
《The Call》說到底,其實就只是「一座動物園重新認識,並且證明自己的過程」,誰規定動物園的保育只能是藉口?誰規定動物園就得靠著消費動物來維繫生計?誰規定動物園只會助長人類對動物的壓迫?誰規定動物園追求商業發展就是膚淺?誰規定動物園賺大錢就沒資格自稱公益團體?SDZG的案例證明了動物園不但可以達成財政方面的永續,更能善用這樣的優勢,插手與滅絕的戰爭,代領地球上的每一個人實踐我們對保育應有的承諾。
不過,別人家的奮鬥史就算看得再精熟,仍然不會變成自己的。在知悉大洋彼岸有這樣的戰友存在後,我們能做出什麼改變?
回看臺灣
臺灣的動物園現階段身處在一個十分尷尬的節點,以檯面上較活躍的幾個動物園為例,雖然園區、形象塑造等外在條件上,相比起亞洲地區多數同行強調野性的手法,確實更貼近歐美的洗練風格,但是卻能從他們發表意見與行事作風的細節部分感覺到,實際上的內在仍然沒有跳脫出古舊的思維。
如果是反過來那倒不怎麼令人擔心,畢竟只要等到契機出現,外在形式的改變不必耗費太長的時間;但若是卡在一個不上不下的位置,卻還被昔日榮光蒙蔽著雙眼,隨著時間過去,即便一時間還能用美好的言詞來包裝實際上的空洞,終究會迎來被看破手腳的一天。
 2014年時,一百週年的臺北動物園打著「Learning from Life」的標語,曾經讓人感受到一絲改變的可能性,但6年過去了,當初的驚喜似乎也與展牌一齊隨著百週年結束而消逝無蹤。
2014年時,一百週年的臺北動物園打著「Learning from Life」的標語,曾經讓人感受到一絲改變的可能性,但6年過去了,當初的驚喜似乎也與展牌一齊隨著百週年結束而消逝無蹤。
處在當今這樣一切發展計劃都必須在對「現行狀態」有所意識並加以考量的前提下部屬,並在途中設置多個階段性終點,且需順應「時局變化」而留有調整彈性的時代,臺灣的動物園和許多先行一步同行們的差距早已不像上世紀末那樣容易填補。
確實,每個組織多少都抱有一些即使會損害發展也不願或不能讓步、揮棄的傳統,或是不得不的苦衷,再者,就如同我在前導文中提到的,動物園的存在多種多樣,沒有所謂哪一種更優越,臺灣的動物園並不需要看到他人的好就盲目追捧或妄自菲薄,畢竟所謂的學習並不意味著攀比,但正因為如此,對於想創造己身價值、被世界看見的臺灣動物園來說,一味模仿行業先進已經緩不濟急,見賢思齊顯得愈發重要,尤其是「思齊」這一環節。
看見學習對象是甚麼樣子是一回事;看出學習對象在做甚麼是另一回事;看懂學習對象怎麼做又是另一回事;說到底,理解學習對象為何這樣做才能算是無愧於學習一詞,而所謂模仿,則是看在那之後能否創造出只屬於自己的版本並付諸實行。但倘若無法學以致用或舉一反三,這些「學習」只會讓人感到空泛且消耗大量成本,甚至到頭來根本宛如一場假借學習之名的拖延。
比起拘泥外在形式、搪塞己身不足或者好高騖遠,那些想要更進一步的臺灣動物園必須先正視問題的存在,看看自己究竟是受困於近期面臨的小挑戰、長期堆積下來的不良體質,亦或者是一時半刻不見希望所在的萬丈深淵。SDZG的案例告訴我們,在思考自己想成為怎樣的動物園、透過他人的案例以及角度來協助自我審視之後,歸根結底,還是回到敢不敢跨出那一步、做出相應的行動,如此而已。
以臺灣的情況來舉例,「徵才時限定本國籍人士」,對於隸屬地方政府的各動物園來說,這項規範本身或許看似問題不大,但若綜合「台灣並沒有任何教授『動物園從業人士所需知識、技術』的學術機構」以及園內確實缺乏許多「動物園發展所需領域的專職」等令人遺憾的事實來看,這個規範就是相當值得被討論的,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自己的TAZA(臺灣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必須擔負起更多責任;與此同時像被三立收購的新頑皮世界這樣私人動物園勢力的崛起,無論是否會對行業的整體生態帶來巨大震盪,仍然提醒了臺灣的動物園們其周遭的環境仍然在不斷改變,絕對不是應該安於現狀、陶醉於過去的時刻。
雖然單憑臺灣現有的動物園體量多半不足以支撐,但包括這本《The Call》的作者創設的Branning Strategies在內,光在「動物園的發展規劃」這一面向,世界上就有著不勝枚舉的顧問公司,更別提那些在全球規模下深耕多年的營養、豐富化道具、展場設計甚至運送專業的「戰友們」,豪不誇張地說,戰備物資與供應商俯拾即是,我們需要做的只是看破「往例」帶來的枷鎖,嘗試加入那些佈局已久的戰線,積極地嘗試把掛在嘴邊多時的潛力兌現。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這本被取名為The Call的書,實際上內容分了至少三分之一來解釋The Lynx的重要性,闡述SDZG為了企及自己所認同的「世界第一」而改變的歷程,不僅說明改變的不易,也提醒外界「頭銜的重量」。
就好像在動物園中進行的飲食調整,起初必定會遭遇反彈,過程中也會經歷許多讓人為自己付出感到不值的打擊,但時間終究會證明當初發起行動的價值。曾經有一位中國網友向我說到,他覺得他們的動物園跟臺灣就差30年,而臺灣跟西方的先進可能也差了30年,現在回看這句話,我不禁想到,這樣的評論只有在前者已開始行動,而後者止步不前的前提下才得以成立,30年後他們追上了我們,那我們呢?
別說跟SDZG並駕,在建築與設備不斷老化又不被重視且缺乏人才的培育基地等現況之下,是否還能撐得起動物園的外衣?
更別說那個若有似無,只存在於願景中的亞洲頂尖、世界一流?
「知,然後行」的前半部分,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問題,對於臺灣的動物園而言相信都是老生常談了,畢竟,國內有的是各領域的專家,但多數能量卻似乎被消耗在繁瑣的行政文書以及想方設法為動物園續命,而非通過動物園得到「增幅」,成為落實保育工作的助力。
越是看著「人家的動物園」,就越發令人感嘆,後半部分的「知行合一」,雖然看上去已經近在眼前,卻似乎比甚麼都要遠,油然而生的無力感,何時才會待到被把握的契機?屆時又得花上幾多個15年去填補缺口?戰線的推進不等人,很多時候必須憑藉一口氣緊巴住不放才能擺脫被甩在後頭的下場。
在這場與滅絕的戰役中,一旦鬆懈,或許就很難再找到機會回到前線了,不管是立場、能力,還是心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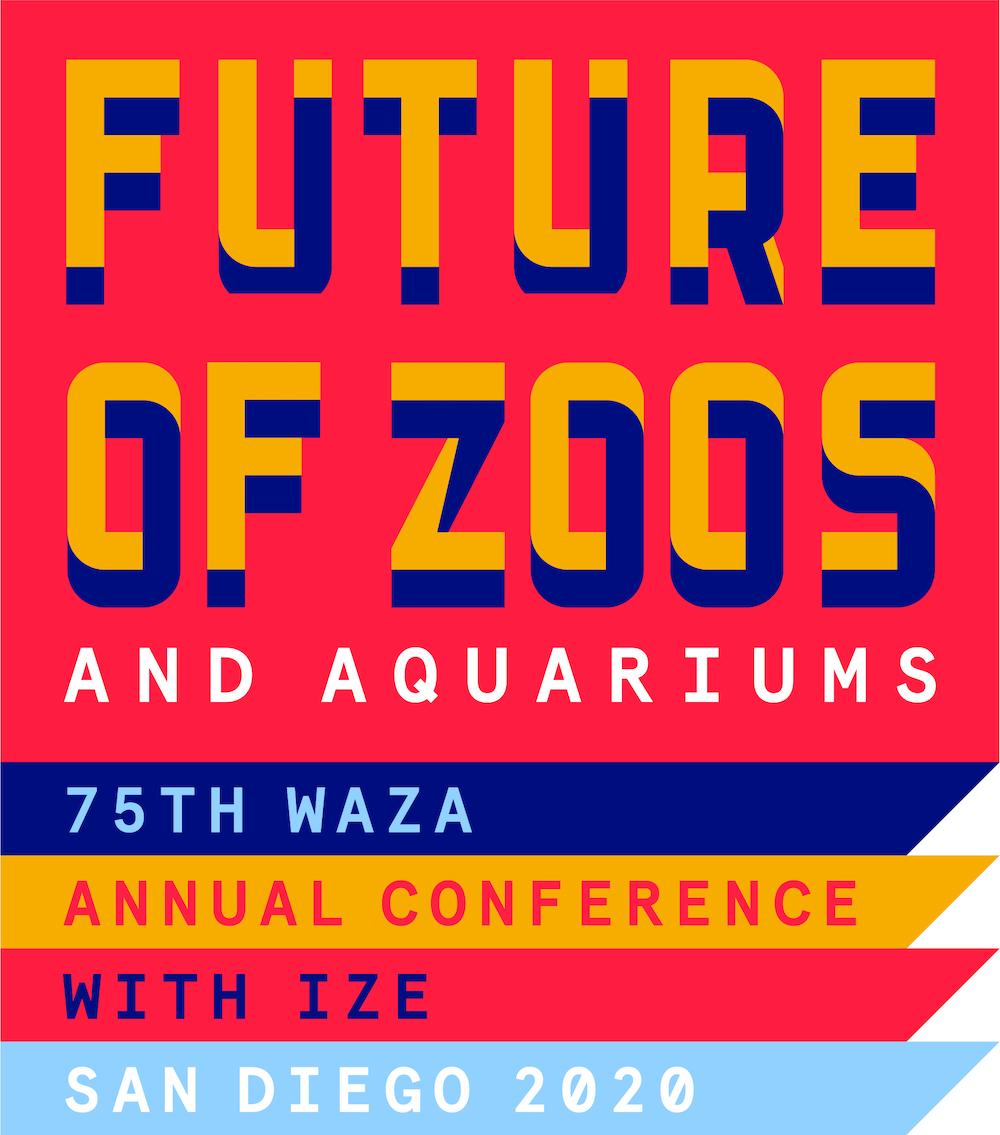
2020年的世界水族館暨動物園協會年會將由SDZG主辦,主題是「動物園的未來」,因為疫情的影響,本屆年會將改採線上直播的方式進行,看到這裡的朋友們十月不妨一同加入看看屆時在台上主持的SDZG與這本2018年出版的書裡的SDZG是不是同樣的?而現在的他們已經走到何處?看向的又是怎樣的未來?










